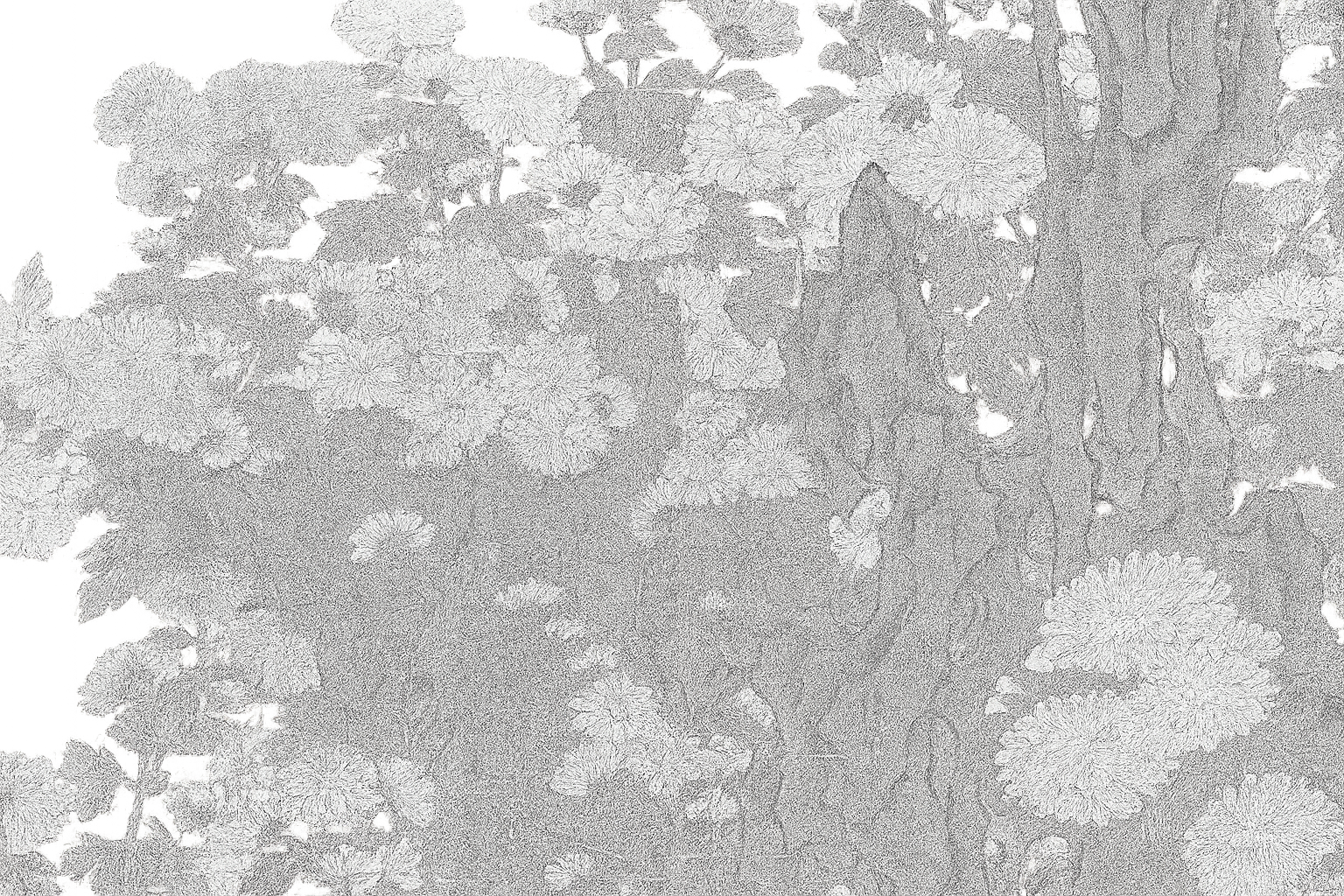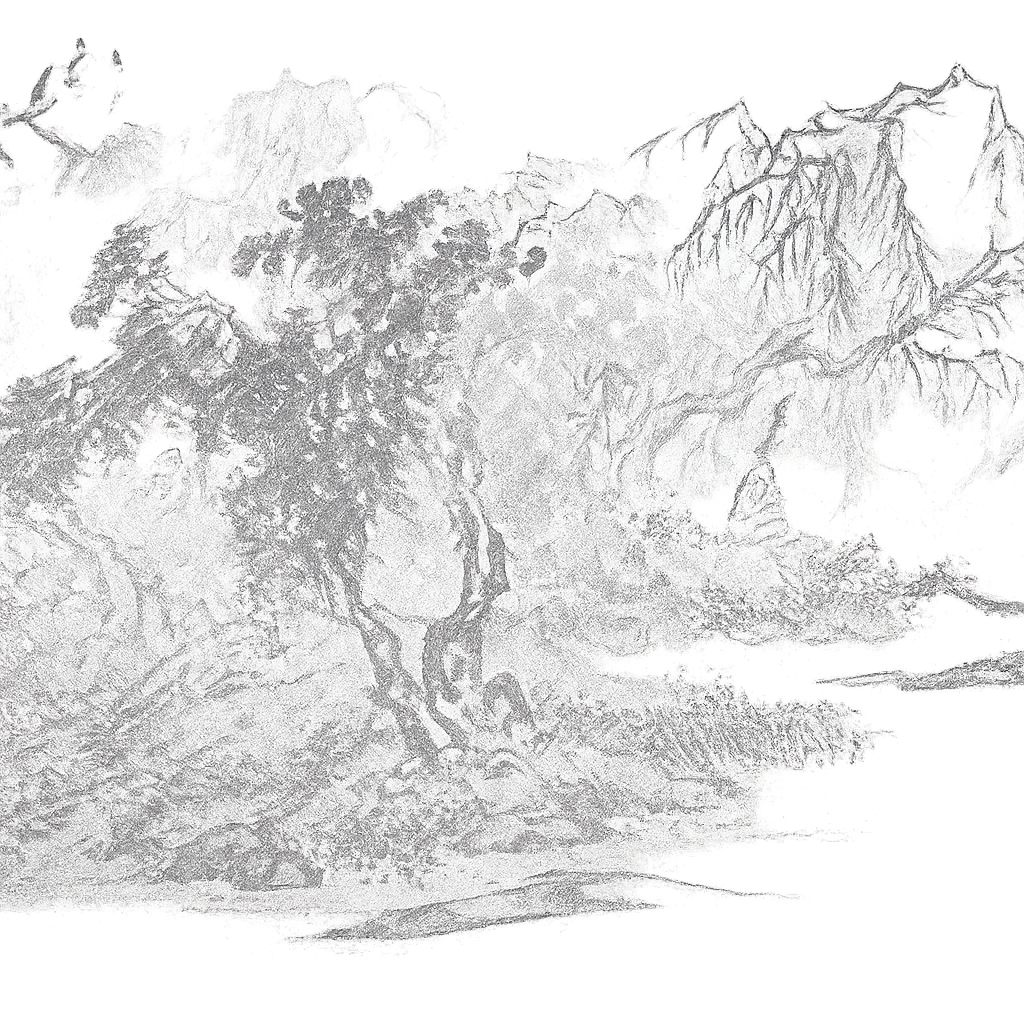周记·其二
除夕 记忆里的年味,好像只存在于小时候。 那时候,人不管散得多远,总会在这一天被拽回同一张饭桌。老人像一枚绳结,把一个大家庭死死系在一个小屋子里。 男人们围坐一圈,高谈阔论,世界局势在酒桌上反复推演;女人们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来回折返,来回穿梭,十分匆忙。 最自在的反倒是我们这群小屁孩。 偶尔被抓去贴窗花、剥韭菜,但更多时候,我们自成一界,游戏时间。 那几年,玩的最多的是 『三国杀』。 几个加起来还不到半百的小孩,偏要学大人运筹帷幄。嘴上动不动就是局势、兵力、反贼忠臣,波云诡谲,说得煞有介事。牌一烂,情绪就先崩,有人脸涨得通红,有人急得抓耳挠腮。 小孩终究是小孩,藏不住气。 局面一旦失控,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——哭。 哭声一起,场面迅速失控,落得一个鸡飞狗跳。 那边,男人们还在彼此强行输出各自的世界观;这边,女人们正忙着油烟滚滚。没有人腾得出手,也没有人真的想腾出手,来处理我们这一烂摊子。 大人们总以为,小孩什么都不懂。 其实小孩对气氛的变化,比谁都敏感,只是说不出来而已。 我记得,是一个比我大一年级的姐姐出面收场。她想了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解决方案。 『向我们展示内裤』 已经忘了当时的我的真实想法, 但是效果出奇地好。 我那个哭得快要背过气去的远房表哥,居然真的就此止住了。 现在回头看,那时候的团聚大概是我记忆里,为数不多的、依靠“物理声波”完成的。 这种热闹,大概只持续了三年。 再往后,手机开始普及。 本该让人更容易说话的工具,反而在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,慢慢砌起了一堵看不见的墙。 人勉强坐一屋子 (基本很难凑齐)。 越来越安静。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对这些聚会生出了一点抵触。 不喜欢被推着去的团圆饭,不喜欢倒计时后密集炸开的鞭炮声,也不喜欢空气里那股散不干净的硫磺味。 一切都太熟练了。 熟练得像一套年年复用的流程。 人们按时落座,按时举杯,按时说吉利话。等热闹退潮,屋子里很快又恢复成各自低头的沉默。 像是完成了一次集体任务。 原子化 这个词,是后来才学会的。 但那种感觉,很早以前就见过了—— 一张圆桌,坐满了人。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屏幕里。 谁也没真正离开, 谁也没真正靠近。 那个笨拙又吵闹的过去,大概是真的回不去了。 所以也只能这样,一年一年地过。 烟花的花样越来越多,春晚的内容越来越烂,团圆饭一年比一年精致。愿望每年都在更新,人也一边羡慕别人,一边被别人羡慕着。 至于那些真正留在过去、带不走的东西—— 好像也只能留在那里了。 总之,新年快乐。 能力圈 “一知半解是件危险的事情; 比埃里圣泉水要深吸, 否则别饮: 浅浅喝几口导致大脑混沌, 痛快畅饮反会使我们清醒。” 亚历山大·蒲柏在诗作《批评论》